摘要:以身份认同的实践性和生成性为理论依据,展现《西藏文学》立足青藏高原的现实发展情状建构其高原文化身份的阶段性探索与实践,具体表现为创刊之初徘徊于政治语境与文化表达的夹缝中自我文学选择,1980年代伴随文化自觉而生成的高蹈扬厉的文学景观,世纪末游离于市场化与文学化之间的艰难抉择,以及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以文化回顾与文学开拓交错的方式所体现出的再造辉煌的强烈诉求。 关键词:《西藏文学》; 高原文化 ;身份认同 ; 自我建构
随着文化研究的勃兴,人们在各种语境中频繁地使用“认同”、解释“认同”、建构“认同”,譬如,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①等。关于认同的概念,“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等人,均将同一(idenity)和差异(difference)相互对照”[1]p129,采用静止的方式展现“认同”的属性,而当代学者科利认为,认同是实践性的和过程生成性的,他将“认同”描述为两种类型,即“固定认同”和“叙述认同”,所谓“固定认同”,就是自我在某一个既定的传统和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given),进而借由“镜像”式的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叙述认同”则是由文化建构、叙事体和时间的累计,而产生的时空脉络中的对应关系,叙述认同经常必须通过主体的叙述以再现自我,并在不断流动的建构与斡旋(mediation)过程中方能实现[1]p129。科利的“认同”观,具有扬弃“认同”传统认知的方法论意义,认为“认同”要么是被赋予的,要么是被建构的;而在传统社会中,经过长时期的建构的“认同”势必会具有强力赋予价值,因此,人类的文化发展其实如德里达的“解构延异”过程一般,处在旧有的文化不断地被分裂,新兴的文化不断形成地去中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地被叙述建构的过程。欧文·塞米尔·史可更明确表示,“身份和他性都包含在并通过叙事来传达”,并且“身份……通过实施、通过行为而存在,也就是利用众多话语工具通过实践来建构的,这些话语工具可以叫做‘身份技术’”[2]p122-123,因此,身份认同是实践性的活动过程,带有浓烈的社会叙述建构意味。若以上述的身份认同观念审视《西藏文学》的身份认同与建构的实践和探索,或会发现在不同时期,其高原文化的认同呈现出不同的建构风貌:创刊之初,《西藏文学》筚路蓝缕,徘徊于政治语境与文化表达的夹缝中自我选择;1980年代,《西藏文学》进入文化自觉高蹈扬厉的喧哗时期;世纪末,《西藏文学》游离于市场化与文学化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惨痛的教训;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以文化回顾与文学开拓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强烈地再造辉煌的诉求。
一
1949年10月,中国作协主管的《人民文学》创刊,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撰写的《创刊词》,可看作既是对毛泽东题词的全面阐释,又在某种程度上规定出新中国文艺期刊的办刊方向、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我们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二、划清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学的界限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是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心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运动。”[3]由此,《人民文学》导引出“人民的文学”的身份建构与身份叙述的意愿,并对新中国的文艺刊物及文学创作、批评、传播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文化影响。对此,吴俊认为“《人民文学》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获得了‘文学国刊’的身份和地位,它的文学和政治使命就是要发表‘示范性的作品’和‘指导性的理论’。它代表的是新的国家政权和国家利益在文学领域的实际体现……《人民文学》的创刊,也就是新政权、新政治和新政策为建构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组织化、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国家最高权力直接介入并支持了刊物创办的整个过程。因此,《人民文学》获得的是国家权力予以充分保障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等等的全面支持。《人民文学》也就不能不被赋予应当而且必须代表或承担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4]。因此,《人民文学》的创刊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新中国其他文学期刊的创办模范,尤其是各省区文联、作协的机关刊物无不以《人民文学》为效仿典范。如1950年11月创刊的《河北文艺》可能是新中国最早出现的省级刊物,在其《发刊词》中明确表述创刊缘由:“八月一日,河北省正式建立了,全省人民的经济建设将要大踏步地前进;文化建设方面,也就随着有了广泛的需要和广泛发展的条件。文艺工作方面,自然也必须适应这个蓬勃发展的形势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河北省文联筹委会,就在这一形势与要求下成立了。文联筹委会成立以来,第一件筹办的事,就是出版一个机关刊物——《河北文艺》”,并确定了刊物的主要任务“要为河北省人民的建设事业服务;为河北省群众的文艺运动服务。因此,它必须用文艺的方法,来发扬河北省广大人民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及各种建设中的新英雄主义,反映人民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籍以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生产热情……并及时地登载当前群众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性的文章”[5]P7。细察其宣示几乎与《人民文学》无异,区别在于地域空间的缩小,着眼于特定行政省区的文化身份的表达,因此《河北文艺》可视为河北版的《人民文学》。而随后成立的《山西文艺》(创刊于1950年5月,终刊与1951年6月)、《山东文艺》(创刊于1950年6月)等省级文艺刊物,其《发刊词》基本上是先国家情态后本省文学发展趋向的表达路径,并在文体编排方面基本类似于《人民文学》 [6] P189。与文联、作协的由上而下的行政编制一般,文艺刊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的文艺金字塔式的结构,就自然出现“文艺刊物……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担负起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6] P185的景象,说明体,也是政治的信号集散地,并规划了文学发展的轨迹。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文学期刊既是文学的载,改革开放前,文艺期刊引发了众多的政治活动或运动。
全国创刊最晚的省级文艺机关刊物当属1977年正式创刊的《西藏文艺》,此时的政治、文学形势,与其他省市区文艺机关刊物成立时略有不同,因此文艺发展的方向与任务的表述有所不同:
《西藏文艺》一定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通过文艺形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前要认真宣传华主席,宣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历史性胜利的伟大意义,狠揭猛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滔天罪行。……
……《西藏文艺》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华主席率领百万农牧民夺取越来越大的胜利,歌颂百万翻身农牧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火热的斗争生活。
……《西藏文艺》要把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作品中要尽可能地采用百万农牧民喜闻乐见的风格和形式,采取群众中生动形象的语言,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西藏特色。
……《西藏文艺》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开门办刊,依靠群众的力量,充分运用批判的武器,认真开展文艺评论,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要使《西藏文艺》真正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在新的一年里,《西藏文艺》一定要坚决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指示,把热情反映深入开展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一中心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努力反映加强党的建设、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为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战斗任务做出贡献![7]
《发刊词》重述党的文艺基本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对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区域性发展和规划的复述,主要强调文艺的政治发展方向,在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语境前提下,提出文学发展的民族化、地域化形式,并对西藏文学的发展提出阶段性的要求。
《西藏文艺》创刊号,共有四个板块。首先是毛泽东、华国锋及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悼念周恩来的文章,意图确立《西藏文艺》紧跟时代步伐、贯彻党委领导的坚强信念;其次是“热烈欢呼华主席 愤怒声讨‘四人帮’”板块,通过文艺形式表现文学参与社会实践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举措;再次是“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板块;最后是表现西藏各行各业发展形势大好的作品。1977年,《西藏文艺》出刊四期,基本上是遵循如是的办刊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高于一切,文学解释政治,政治热情高于文学激情。对于《西藏文艺》的此种言说方式,尽管体现出浓重的文学诠解政治的特点,但也符合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向。即便如此,《西藏文艺》刊发的一些作品也体现出某些明显的文学性,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学的色彩,如对西藏农区、牧区生活的刻画,对农牧民思想观念转变的细微描述,侧重西藏风情的描绘等,为西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平实的基础。代表性作品有许树仁执笔的《织机上的电光》(1977年2期),这是一篇西藏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德吉措姆的《骏马飞奔》(1977年2期)反映的是农牧区革命青年勇斗潜伏的敌对分子的故事,塑造了新西藏培养的年轻女干部琼达的光辉形象;汪承栋的叙事长诗《雪山风暴》(1977年4期)以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为素材,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英勇的西藏人民和驻守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勇斗叛乱分子的历史画卷;索朗顿珠的《阿佳次仁拉姆》(1977年4期)则书写的是夫妻劳模拼干劲、争创优质水利工程的故事。总体上说,这一年的《西藏文艺》大致汇集了十七年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风味,塑造出一大批伴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而涌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及至1978年,《西藏文艺》的文学期刊的文艺趣味始有所改观,尽管坚持政治性为第一原则,但对文艺类型也有所探索,要求稿件“反映我区各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活和动人事迹等各种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曲艺、电影文学剧本、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歌曲、美术和摄影等作品及阐述马列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的文章、文艺评论”[8]。如是,《西藏文艺》对稿件提出明确要求,首先是地域性,其次是历史性,再次是思想性,最后是文艺性或者说是文学性,体现出自觉地整理和梳理西藏历史文化的文学诉求,从全新的角度试图建构出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文学表达样式;而表现形式方面,则是极具有包容性,只要是符合纸媒表现的样式即可,大致就是文字性的和图画(像)性的两种类型。本年度,《西藏文艺》的高原文化自我认同开始萌芽,但总体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佳作较少,究其原因,作家队伍建设正处于草创阶段,作者的文学书写还处于自发状态,作品大部分是激情之作,缺乏思想、情感、形式方面的沉潜。
1979年《西藏文艺》迎来了文学的初春,西藏本土老作家的复出和各民族年轻作家的不断涌现,改变了《西藏文艺》的既有格局,如扎西达娃的《沉默》、刘克的《苍姆决》、刘汉君的《故土》、杨星火的《致老西藏》等作品,完全是立足于西藏高原的本土生活,表现这片热土上发生的故事,热情地关注西藏的昨天和今天,并且有意识地自我反思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代表性的是扎西达娃的《沉默》(1979年1期),该作不同于内地的伤痕表达,而是以极大的勇气书写“文革”对青年人思想方面的戕害,但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有意识地将故事背景设置为“四五”悼念周总理而引发的与恶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表达出沉默中爆发的思想观念。而且,扎西达娃采用欲扬先抑的表达手法,抽丝剥茧般还原殷华、海萍的斗争历程。《沉默》不仅是西藏第一部伤痕书写之作,并且开启了西藏的反思文学的先河。老作家刘汉君的《故土》(1979年3期)描述了旅居国外的藏胞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在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题材,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在西藏文坛实属难得,扩大了西藏文学的书写范围②。种种努力表明《西藏文艺》文学期刊的政治气息逐步让位于文学味道,有力的证据是,1979年《<西藏文艺>改刊启事》中宣扬“《西藏文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文艺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力求题材、体裁、风格和形式多样化,使刊物更加丰富多彩,清新活泼,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西藏文艺》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将十分重视西藏民族地区的特点,继承民族的和民间的文艺遗产,发展西藏民族文艺,使刊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9],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学自我定位,文艺形式的多样化,是《西藏文艺》高原文化认同历程中坚实的一步,也使得晚生的《西藏文艺》迅速成为同类期刊的佼佼者。
1980年相继召开了民族省区和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踌躇满志的《西藏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民族地区的文学刊物要提高质量,还必须遵循党的民族政策,把刊物办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题材上侧重反映本地区各族人民的斗争生活,描绘我们万里高原的独特风光和风土人情,尤其要着力塑造具有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素质的各种典型人物形象”,并提出“争取使我们的刊物开出新生面,早日成为一株独具风姿的高山雪莲”[10]的奋斗目光,进一步明确了《西藏文艺》地域性、民族性的高原文化认同。而同年举行的西藏首次文学作品评选活动落下帷幕,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9月西藏各族作家公开发表的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中,共遴选出81篇(部)优秀作品,其中“不少的作品主要描写了藏族人民的生活,具有较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值得称道的是“藏族作者、作家就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藏族青年。他们熟悉本地区、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勇于探索,勇于实践”[11]。《西藏文艺》刊发的多篇作品入选,其中有6篇入选一等奖③,其中年轻作家扎西达娃的《朝佛》(1980年4期)表达了新时期年轻人的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传统的将幸福寄托于朝佛,祈求来世的幸福,一种是开拓创新,凭借科学文化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展现出新时期的西藏年轻一代昂扬向上的生活姿态。与《朝佛》相似的作品是德吉措姆的《茫茫转经路》(1980年6期),该作获得首次西藏文学评选二等奖,但《茫茫转经路》是以两代人不同的朝佛态度折射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下,穷苦群众悲惨的生活情态,与《朝佛》相比,该作的现实性略逊一筹。但透过西藏首次文学作品评选活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西藏文学的创作队伍开始出现新的变化,高原文化表达开始成为《西藏文学》创作者们自觉的文学观念,而且作品的民族性、地域性表现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深入,开始摆脱政治文化单一表达的藩篱,转而描述和挖掘西藏民众日常的世俗的普通的生活情态,高原文化的表现出现了质的提升,因此,可以说《西藏文艺》的高原文化认同实践初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
1981年,《西藏文艺》的高原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栏目设置上,通过栏目的设置有意识地引领创作方向,设置诸如高原速写、高原放歌、雪山寄情、藏族作者诗歌专辑、藏族作者小说专辑等,集束式地推出展现西藏风情、风貌的作品,凸显新时期西藏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迁以及各族群众的精神面貌;同时《西藏文艺》有意识地培养青年作者群体的努力初见成效,涌现出一批民族年轻作家,为高原文化的建构与书写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当年召开的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西藏文艺界的成绩,认为建国三十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文艺队伍,采取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西藏“所处的地理环境,经历的历史道路,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创作出“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12],又提出西藏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远景规划,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推进西藏文艺的繁荣。此次会议具有拨乱反正的文化意义,在事实上提升了西藏文学的发展信念,检阅了文学创作队伍,坚定了立足西藏、反映西藏、书写西藏的文化立场,为西藏文学的深入发展和文学繁荣奠定了基础。
1982年第2期,《西藏文艺》期望“从形式到内容,力争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表现在对稿件文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开启西藏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征程。就小说方面而言,《西藏文艺》提出“要广开题材领域,重点反映‘今天’。重点反映农牧区。力求发稿‘短、精、深’,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新颖感”[13],对“今天”的关注可谓是当时西藏文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文学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及时地捕捉生活的新气象、新内容,反映新时期西藏新面貌,而短篇小说恰好具备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文体特色;另外,此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短篇小说创作已蔚然成风,佳作迭出,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西藏文学的短篇小说文体探索势在必行。就其具体的文学成效,检索1982年第二期到第六期的小说作品,编次如下:
第二期共刊发10篇小说,包括益希单增长篇连载《推翻誓言的人》,两篇外国文学作品,三篇处女座包括色波的《海螺号吹响了》,其他为扎西达娃的《沉寂的正午》、土登吉美的《归国记》、叶晞的《野驴江嘎和江玛》、雷建政的《圣光莫及的一隅》。第三期刊发小说有色波的《乌姬巴勇》、扎西达娃的《导演与色珍》、益希单增的长篇连载《阴谋者的心思》以及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的《我的恋母情结》等。第四期刊发益希单增长篇选载《贵夫人的忧愁》、金志国的《山石》、张世明的《没有笑脸的平措》等。第五期刊发有扎西达娃的《江那边》、李文珊的《船客》、金志国的《帕珠》、许明扬的《老兵张德山》及印度作家阿西夏·辛哈的《送客进城》等。第六期刊发有扎西达娃的《白杨树·花环·梦》、金志国的《梦,遗落在草原上》、益希单增长篇选载《奖赏与惩罚》、韩明镜的《拐子扎西》、张新力的《阿民留下的素描》及印度作家阿西夏·辛哈的《食人兽》等。
以上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体,意味着西藏本土的作家日益成熟,开始从多个方面深切地关注西藏的社会变迁,及西藏各族群众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情态而表现出的多样的文化情怀;而且,新一代的西藏作家如扎西达娃、金志国、色波等人以耀眼的文学写作姿态伫立于小说创作领域,亦开始自觉地探求符合自我表达习惯的新兴的文学叙述方式,西藏的小说文体发展迎来大发展、大爆发;再次,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荐,也标志着西藏文学的视野不仅仅限于对国内其他省区文学创作的追随,更要直接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开创具有西藏特色的小说文体。
1982的努力也从侧面透露出《西藏文艺》的高原文化的自我建设的创新,不仅立足西藏的历史文化,更要关切西藏的当代表达;不仅努力缩小与全国各省区的文学发展差距,更着力于创新文学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扎西达娃和金志国的“梦”的书写,直接开启了西藏新小说的创作路径,引领一大批西藏作家的文体创新,最终在1980年代中期迎来了西藏文学的魔幻写作的高潮,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震撼。
同时,在198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一大批内地的大学生怀揣梦想,先后走上青藏高原,震撼于高原壮美的风光的同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西藏的感受,或是深层次的,或者是仅以西藏为背景表现内在世界的丰富、复杂,无论哪一种形式,他们的写作为西藏文学注入了活力,他们的探索引起了西藏文学的反思,他们与西藏本土作家一道,引发了西藏文学书写的小高潮,时至今日,依然为文坛津津乐道,其代表性的成果为1985年6期《西藏文学》的“魔幻小说特辑”,推出扎西达娃、色波、金志国、刘伟、李启达等五位作家的作品,独特的叙述方式、别样的文学表达手法,打破了文学叙事的常规。有感于此种西藏文学的发展态势,《西藏文学》的《编后语》提出一个问题——“写西藏的文学作品,如何能表达其形态神韵呢?”并赋予“魔幻”一词极具西藏特色的解释:
所谓“魔幻”,看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 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凡来西藏的外乡人,只要他还敏锐,不免时常感受到那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感、新鲜感、怪异感;浓烈的宗教、神话氛围中,仿佛连自己也神乎其神了。……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滞重的永恒感。[14]
魔幻现实主义或魔幻手法,是西藏文坛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份厚礼,至此,西藏文学以全新的姿态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另外,“西藏的外乡人”也不断地为西藏文坛贡献虔诚的敬意,为此,《西藏文学》在1986年1期推出《进藏大学生专号》、2期推出《在藏大学生专号》。进藏大学生主要是内地进藏工作的大学生群体,在藏大学生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早期和1980年代进藏工作的大学生、短期在藏停留的大学生,还包括完成大学学业之后返回西藏工作的各族本土大学生,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龚巧明、马原、通嘎、徐明旭、李雅平、孙丹年、周韶西、廖东凡等人,在内地和藏地生活的丰富体验,使得以上作家不断地自觉地处于内地文化与高原本土文化的融会贯通之中,使得他们的写作显得尤为厚重,也更充满激情和反思意识。
也就是在1986年,《西藏文学》几乎每一期都推出专号或特辑,除了上述的大学生专号,还有4期的“旅游文学专号”、6期“藏族小说专号”、8期的“藏族古典文学专号”、9期的“诗歌 散文专辑”等,大量专号或特辑的出现,表明西藏文学创作队伍规模扩大,文学作品书写的类型多样,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作家们的写作处于亢奋状态。当然,这种情势既与当时整个西藏乃至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也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温床关系密切,当时不可否认的是《西藏文学》的平台作用、引领作用、示范作用,直接推动西藏文学的常态化发展和跨越式迈进。
同年,《西藏文学》纪念创刊十年,在回顾中指出“《西藏文学》的十年,由季刊到双月刊到月刊,园地逐渐拓宽,共发现和培植藏、汉、回、门巴、珞巴、满、蒙、土家、纳西、朝鲜等各民族作者七百余人次,发表各类作品三千余件,计达百千万字”,可以说,《西藏文学》折射出“西藏新时期文学怎样如滴水成溪,如荒原泛绿,如地热泉仰天喷溅,如碧空散落的天雨花”[15]。于小冬曾创作油画作品《干杯西藏》,基本囊括了当时在西藏文艺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他们是马丽华、王海燕、李知宝、罗浩、李新建、色波、冯少华、皮皮、车刚、韩书力、贺中、龚巧明、田文、洪历伟、马原、于小冬、牟森、扎西达娃、金志国、刘伟、李彦平、裴庄欣、曹勇等人,这一批代表性的艺术家在1980年代以各自的艺术创作支撑起西藏文艺的宏伟大厦,该画作可视为彼时西藏文艺、西藏文学的高原文化认同与建构丰硕成果的象征。
整体上看,1980年代《西藏文学》在建构西藏文学格局的同时,亦在不断地更新和建构文学的高原文化认同,创设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的、以地域文化建设为中心的不断的适应西藏社会发展形式的全新的文化结构,该种高原文化格局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包容性,而非单一的狭窄的片面的民族文化的宣扬。
三
1990年代,《西藏文学》基本延续1980年代的高原文化认同与建构模式,极力维护和打造期刊的文化品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破冰前行打破了西藏的计划经济社会格局,文学的市场化、人才的流动性、纸媒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藏文学》的文学建构模式,致使《西藏文学》的高原文化建构与表达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
从作家队伍看,深受西藏高原文化浸润的作家们逐渐远离西藏,远离西藏的文学书写,逐渐以别样的方式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如马原的出走、皮皮的远去、扎西达娃的转向等,也就说于小冬的画作《干杯西藏》成为西藏文学1980年代辉煌的“最后的晚餐”,人才的流失对西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断层式的影响,《西藏文学》的文学先锋姿态严重受阻,影响力式微。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数量仍然较为可观,作品整体品格相对1980年代更为朴实、更为沉稳,并且年轻作家尤其是新一代藏族年轻作家不断涌现。但总体上说,《西藏文学》的发展态势已趋缓慢,并开始出现落后于同一时期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端倪。
从刊发的作品品格上看,作家们开始重新挖掘西藏特有的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风光景致,写作范围有所收缩,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基本延续魔幻的写作手法、新小说的写作路径,或者说进入到后扎西达娃、后马原时代,作品对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城市化变迁着眼较少,更遑论对城市民众内在世界的深入挖掘,或可称之为乡土的西藏书写。究其原因,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欠发达的交通使得西藏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远离文化的中心,对1990年代的社会发展趋势缺乏将基本的认知,人们大都还沉浸在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中,或者说,作家们还在咀嚼、消化1980年代的文化食粮。因此,突如其来的社会变化,即便是身处内地的作家也是措手不及,更遑论西藏作家呢?西藏的文学界需要静观时代的变迁,于是,有意识的探索暂时处于沉潜状态,待时而发。
即便如此,我们若沿着《西藏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仍可发现《西藏文学》坚守高原文化的努力与付出。在作家队伍严重流失的情况下,《西藏文学》刊发了大量的藏族年轻作家的作品,扶持他们的成长,如扎西班典的《亚大黄叶》、次仁罗布的《罗孜的船夫》刊发后,时任主编李佳俊及时撰写评论文章,热情讴歌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并预言“从扎西班典、次仁罗布身上看到一个新的信息:继益希单增、拉巴平措、班觉、恰白、赤旦严措;扎西达娃、色波、央珍之后,又一代藏族青年作家闯进了西藏文坛。虽然还难免几分稚嫩,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创作热情,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艺术开拓精神,必将给蓬勃发展的当代藏族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惟其稚嫩,更具希望,应当受到关注”[16]。在此,李佳俊传达的恐怕不仅仅是对藏族年轻作家的关注,更是希望有更多的藏族人士或者是文学爱好者参与西藏文学的建设,张扬西藏本土文学的艺术价值。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以白玛娜珍、梅卓、格央等为代表的藏族女作家登上了西藏文学的舞台,以女性的视角书写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嬗变,展现西藏女性隐微的内在世界,显示出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这一时期《西藏文学》高原文化建构的路径。
1992年3期,《西藏文学》开辟“蓝天诗潮”栏目,这是继“雪野诗”之后的又一次诗歌文体的积极建设。相比较雪野诗而言,蓝天诗不为论者所关注,其实,在精神气质上,蓝天诗承嗣雪野诗的表达路径,彰显西藏的文化特质,只不过,相较雪野诗而言,蓝天诗缺乏开拓、张扬、磅礴的精神气势,对时代的精神把握欠缺,而最终成为西藏风光的吟咏、个人心灵的呢喃。为了挽回颓势、再现西藏诗歌创作的辉煌,《西藏文学》1995年2期推出诗歌专号,刊发了中外53位(组)诗人的作品,不再局限于高原文化的表达,而强调多元化的精神碰撞、多样化的言语火花的集结,堪为诗坛盛事,但由于后续写作乏力,评论一定程度的缺席,这一期的诗歌专号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成为《西藏文学》诗歌写作的绝响。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发展局面下,《西藏文学》2000年的市场化探索才显得弥足珍贵,这是其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坚守高原文化、确证自我高原文化身份的确证。但由于《西藏文学》的身份转换太突然,又由于摒弃了文学的立场而选择了文化传播的发展方向,导致出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致使《西藏文学》的高原文化建构愈发缓慢,愈来愈强调文学表达的地域化、民族性,甚至出现画地为牢的现象,在看似喧嚣其实是自娱自乐的幻象中踽踽前向。经过几年的沉潜和消化,《西藏文学》方走出这一事件的阴影,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境况,一方面通过不断地设置新栏目、推出新作品来重新展现高原文化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全新的组稿方式,譬如主动预约作家创作、主动召开作家作品研讨会、主动与兄弟省区文联联系推出各地专辑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确定了《西藏文学》的办刊信念,坚定了办刊方向。另外,《西藏文学》积极主动参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建构,如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文学》刊发了一批庆祝类的文学作品,并且,随着内地游客的大量涌入,西藏的山水自然人文景观成为人们写作的重点,《西藏文学》及时组织编发大量的游记感怀类散文,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西藏景观表达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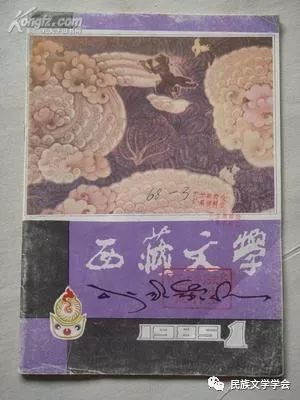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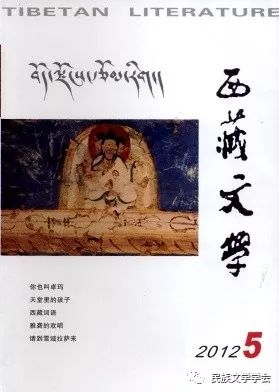
在三十多年的办刊历程中,《西藏文学》通过一系列的文学实践,不断地塑造、修正自我的高原文化身份,尽管历经沧桑,但确定不移的是坚持刊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凸显西藏区位特点以促进西藏文学的发展态势。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氛围的不断嬗变,高原文化的活态流动性,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日益突出,但立足高原、表现高原、塑造高原的文化气质和文学秉性是《西藏文学》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因此,《西藏文学》既要避免对高原文学的概念性界定,过份地强调民族性不利于《西藏文学》整体的良性发展,也要避免刻意地瞩目西藏的区域化设置,自设壁垒同样无助于刊物的长足发展,可行的路径就是目前《西藏文学》的立足西藏,辐射少数民族地区,打造具有青藏高原气息的运营模式。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藏项目“新世纪《西藏文学》(2000—2011)意识形态的表达与诠释”(13XZJC751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陶家俊认为:“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而言,在个体认同的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降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在其看来,“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参见陶氏《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2期,第37—38页。
②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类似于《故土》之类的书写海外藏胞生活情态及其故土情怀的作品在西藏当代文学殊为罕见,未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
③分别是《故土》(刘汉君)、《朝佛》(扎西达娃)、《雪山风暴》(汪承栋)、《像雄浑浪漫的草原那样美》(张隆高)《花园里的争议》(班觉,藏文)、《冬季之高原》(恰白·次旦平措,藏文)。
参考文献:
[1] 廖炳惠.关键词200[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6.
[2] [美]于连·沃夫莱,陈永国译: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茅盾.创刊词[J].人民文学,1949(10).
[4] 吴俊.《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J].扬子江评论,2007(1).
[5]刘宏权、刘洪泽.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6]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7]发刊词[J].西藏文艺,1977(1).
[8]稿约[J].西藏文艺,1978(1).
[9]《西藏文艺》改刊启事[J].西藏文艺,1979(3).
[10]本刊评论员.团结友爱的盛会 继续进军的号鼓——祝贺九个兄弟民族省区及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的召开[J].西藏文艺,1980(3).
[11]薛元超.西藏首次文学作品评选揭晓[J].西藏文艺,1980(6).
[12]拉巴平措.团结起来,为繁荣我区社会主义民族文艺而奋斗——在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J].西藏文艺,1981(6).
[13]《西藏文艺》编辑部.新春寄语[J].西藏文艺,1982(2).
[14]编者.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写法试试——本期魔幻小说编后[J].西藏文艺,1985(6).
[15]本刊编辑部.《西藏文学》十年[J].西藏文学,1986(10、11合刊).
[16]黎愚.喜读《罗孜的船夫》[J].西藏文学,1992(4).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魏春春,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西藏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
值班编辑:和亚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