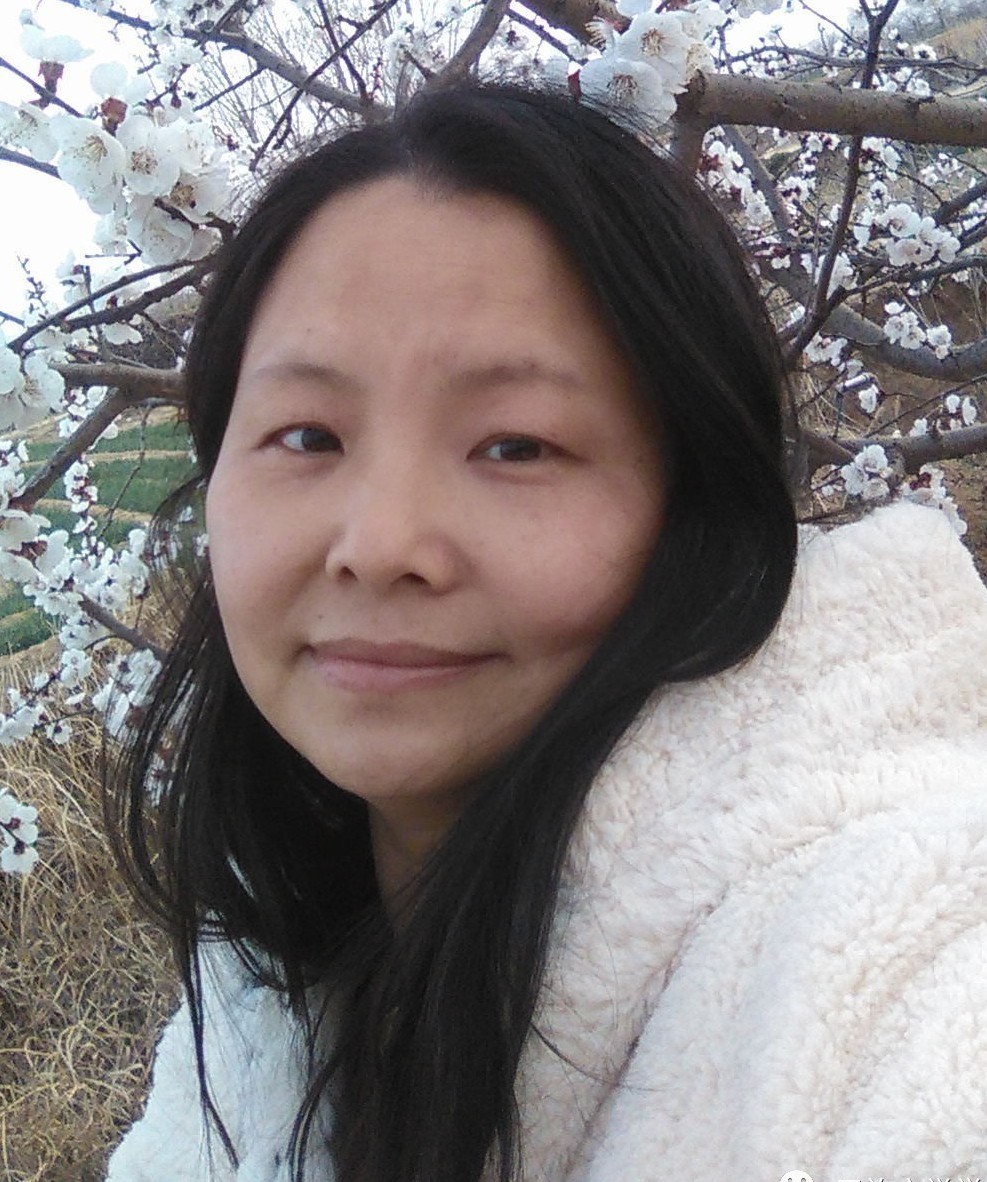
沈秀英:凡俗与宗教:论石舒清主体精神的两个世界
内容提要:石舒清的笔下存在着两个相对的世界。一个是写实的、纷扰不宁的凡俗世界,另一个是求圣、求真的宗教世界。两个世界背后是石舒清两种身份的写作: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和作为回民族一分子的写作。他用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眼光打量着作为普通乡村社会一角展现的回族的凡俗生活;用伊斯兰文化育养的宗教情怀打量着回回民族的精神世界。宗教情绪是他的根本情绪。石舒清通过文学创作成为了真正的回族生活的记录者和回民族精神的代言人。
关键词:石舒清;写作视角;宗教情怀
回族作家石舒清,1963年生人,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石舒清已出版《伏天》、《苦土》、《开花的院子》、《暗处的力量》、《底片》、《灰袍子》等多部小说集,有的作品被译为法文、日文、俄文等。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第十一届庄重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他是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宁夏文学的一面旗帜。
作为回族人,石舒清有深刻的民族认同感,并把它作为构建自己作家身份的重要一维。石舒清在读《古代回族诗选》时曾说:“皇皇一册《古代回族诗选》,辑入29位诗人的百余首诗,但一路看下来,竟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任何一首诗作写到回族和回族生活。”石舒清对于一本所谓的专门的回族诗选竟没有一首诗作写到回族和回族生活,感到不满、遗憾,甚至耿耿于怀。石舒清想做一个真正的回族和回族生活的抒写者,他曾经深情表白:“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我更庆幸我是一个回族作者……回回民族,这个强劲而又内向的民族有着许多不曾表达难以表达的内心的声音。这就使得我的小说有无尽的资源。”石舒清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民族生活的记录者,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代言人。他立意用作品向外界传递来自西海固的回回民族的声音。
于是当我们考察石舒清的小说画卷时,就发现隐隐存在着两个相对的世界。一个是写实的、纷扰不宁的凡俗世界。从这个世界,我们几乎看不出这是个伊斯兰的世界,这儿的人们像别处的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存在欺压、困顿、苦难、哀伤和欲望。另一个是求圣、求真的宗教境界。这个世界里宗教理想引领人的精神生活,脱离世俗,让灵魂走向高处。这两个世界都是回回民族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生活都是现实中回民所过的生活。它们拼在一起勾画出了当今商品化社会里偏远的西海固地区回民完整的生存状态。
玛乔丽·博尔顿说:“故事不能自我讲述,不论谁讲故事,为了达到讲述的目的,他总得站在一定的相关的位置才行.”审视他笔下的这个世界时,我们发现他写作所站立的位置并非纯粹的回回视角,两个世界背后是石舒清两种身份的写作: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和作为回民族一分子的写作。他用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眼光打量着作为普通乡村社会一角展现的回族的凡俗生活;用伊斯兰文化育养的宗教情怀打量着回回民族的精神世界。
一、乡村社会的凡俗世界: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眼光
石舒清的创作并非是无本之木,故乡给了他笔下的两个世界。石舒清曾把自己的书写对象概括为“吾土吾民”,他说:“我非常喜欢、心疼那一块土地和生息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隔一段时间回去,见到的每一张脸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好像他们一律是你的亲人。”这块土地是贫寒的,生息在这土地上的让他熟悉亲切的人大多是平常的小人物:懒汉、哑巴、看守庄稼的眼睛有毛病的叫望天子的老人……石舒清用深情的目光凝望他们,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弱者的同情。但他也如实写出了乡亲们在利益和生存面前表现出来的困顿、挣扎和势利气。这种势利、挣扎和困顿并不是发生在恶人和恶人之间,或者发生在恶人与善人之间,有时就发生在善良人的身上,发生在弱者和弱者之间。于是这伤害就来得尤其尖锐,让心疼痛。长篇小说《底片》“物忆”部分的《四十房土蜂》中写道,“我”家的土蜂分窝飞到了哑巴家去了。这使得父亲不大痛快,对蜂子有些恨意了。因为哑巴家一堆儿女日月不好没有男人,在村子里是没有地位的。如果能飞到亲戚家或者队长会计家就好了,因为可以算是无形中送了他们一份礼物。父亲是善良的,现实是残酷的。生存的选择使得父亲希望蜂子能飞到亲戚家或者队长会计家,以讨好亲戚或队长会计,不曾想去了哑巴家。父亲心里的不痛快、对蜂子的恨意,是善良人无形中对弱者的歧视,是弱者对弱者的歧视。而这又是多么悲凉的啊!石舒清同情哑巴,也理解父亲,也不想过分指责父亲,心底微妙的情绪波动中是现实的无奈和无语。
在这个乡村社会里,人的精神是萎缩和麻木的。村人们浑浑噩噩,没有任何自觉意识。人像动物一样活着,不知道原与委,也不想弄清楚原与委。《选举》中的鸡肠子河村在经历闹剧般的选举后,村民“纷纷责备着选刘有财当村长的人,可终了却不知究竟是谁选举了刘有财,又是谁罢免了巴掌脸”。最后“巴掌脸”依旧是村长,而鸡肠子河“也自然还是鸡肠子河”。作者对村子落后滞缓状态的描述痛彻心扉:“走离鸡肠子河,一百步,回头看,村子就极像一个马圈的废墟”,又“像烈日下的瘦狗一样贴在地上,没一点指望与梦想地睡着了”,在这里,“一切都那么的无精打采,奄奄一息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时间在这里死了”。人们像马、像狗一样地生活,没有思考,没有指望,姑且活着,日子循环重复没有变化,像废弃的荒圈。石舒清刻画的这个世界严峻沉重,没有生机和活力。生活的残酷在这个群体身上留下的是与别处一样的印痕:斤斤计较、麻木、见识短浅、愚昧……。此时,石舒清的写作视角是非宗教的。
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眼光审视着自己本民族的世界。现代教育让石舒清成长为拥有现代知识和智慧的一介文人。通过读书,石舒清更多地受到鲁迅的影响。郎伟发掘出鲁迅对石舒清的深刻影响:“这种对于鲁迅精神的由衷亲近和继承,使石舒清对正在行进着的中国西北地区的乡土生活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认识和理解。当这种认识和理解化为作者笔下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时,石舒清的小说便具有了相当的思想锐气和穿透力。”这些现代知识文化相对于他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说是异质性的,这使得他不再以纯粹回族人的思维范式看世界,而是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者的眼光看问题。他打量本民族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时,也不再是纯粹的内部眼光,而是以启蒙者的眼光,带有部分局外人的眼光回头审视自己的回族世界。石舒清可能没有鲁迅语言的犀利和独特,但是石舒清小说仍然具有穿透力,这种穿透力是隐藏的。石舒清的书写更多地不动声色:写他们的认真、现实、坚强;写他们的麻木、隐忍、愚昧。石舒清站在现代的高处回视自己亲近的故乡,他无力改变环境,只有将痛心和哀伤,寄予笔端,展现故乡的真实面目,“揭出病苦”,旨归自然也是“为了疗救的注意”。我觉得他写作中有着更多的20年代乡土小说的影子。他以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给自己的父老乡亲以“人文”的关怀。
石舒清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出对人性的尊重与宽容。《果院》中耶尔古拜女人对年轻的园艺师有着大胆的期待。当果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并且几道门都半掩着时,她甚至有挑衅的意思,“她当时手里有一个小土块,她把它攥得湿湿的,她是想着用这个打一下他的”。对信仰伊斯兰的教民而言,这种情欲是暧昧的,不被准许的,应当受到谴责的。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身净”、“口净”、“目净”、“食净”。行文中我看不出石舒清的谴责,相反石舒清很宽容,对耶尔古拜女人更多的是理解之同情。所以石舒清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着宽容精神的人,有着尊重人性的人文情怀。
石舒清的人文情怀还更多地表现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他刻画了许多心灵美丽的女子,赞扬他们的坚韧和耐劳;但又对她们的过早负重、青春易逝、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被虐待而同情而哀伤。不说旁人,就拿他自己身边的女性来说吧。长篇小说《底片》的《奶奶》一文中,奶奶活了39岁,没享上一天的福,受了一世的罪。奶奶偷着给饿得粘在门口不走的背上背着小弟弟的妹妹馍馍,结果被爷爷用楦鞋的木楦头砸得昏死过去。爷爷在外面跑久了,有些轻看奶奶。有时候动手打奶奶。最厉害的一次竟用秤砣把奶奶打得昏了过去,最后用冷水激活过来。后来爷爷被劳改,奶奶最终是愁死、累死的,她在提水的时候倒下了,仓促地离开了人世。《底片》“痕迹”部分的《月夜》一文中,父亲经常打母亲,脾气暴躁,一次竟然拿刀砍在母亲的额边。几十年过去,如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痕留在母亲脸上。《底片》“母亲家的故事”《外奶奶》一文中,外奶奶燎牛头,因为没有把好火候,把牛头烫破一大块。外爷抓起烧红的铲锅,一下子就按在了外奶奶的脖子里。
被虐待者是自己的亲人,施虐的人也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只是静静叙述,冷静而悲悯。对这些女性们的遭遇石舒清深含同情;对于作为施虐者的亲人,石舒清又无法谴责他们,无法恨他们,“他们一一有着他们的苦楚”,而且这些亲人在外面的举止有时可以担得上“仗义”二字,甚至曾做出惊天动地的让本民族都敬佩的事来。我们只能感慨,一个民族有了信仰,这个信仰让他们向真、向善、向美,珍视灵魂和生命,但现实的疲惫不堪和缺乏让他们变得麻木、愚钝、保守、封闭、缺乏幻想和创造,甚至让他们漠视生命。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石舒清的心灵充满着文人的忧伤和惆怅。他的心灵是那么柔软,即便是“一群鸟儿从城市上空飞过,飞得很高,好像和下面的城市没有关系。他的目光常常被它们带向很远。心里因此有一些怀恋和惆怅,又不清楚怀恋的是什么,惆怅的是什么。也想不清鸟儿们飞去哪里了,只是觉得它们是在向远处飞去,觉得它们会一直飞着,停不下来,无法停下来。”他就用这样柔软的温情、温润的悲悯审视故乡和故乡的人,呼唤回回民族更好的生存。
二、回回民族的宗教世界:伊斯兰文化育养的心灵追求
西海固是一块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很深的土地,这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给人们的生活以种种启迪和暗示。石舒清自幼生长在伊斯兰氛围浓郁的回族聚居区,宗教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沉淀在他思想的深处。石舒清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充满了敬意与虔诚。宗教情绪就此成为他人生坚实的磐石,对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宗教世界是石舒清打造的核心境界;宗教归属是石舒清的最终向往。
石舒清眷恋充满神性的生活。“人是多少需要一些神性的,神性带与人的,惟有幸福。”这种神性的获得途径之一是冥想。冥想是自觉的灵魂的自我拷问,以宗教的方式洁净自己从尘世带来的污浊。石舒清的宗教神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在24岁的时候就开始冥思死亡。“不知始于何时,青年的我竟漠然于谋求生计,却无缘无故地、徒劳地冥想生命与死亡一类。越想越糊涂。越糊涂越绝望。绝望成了一道厚实而不可逾越的障蔽,使我几至窒息。我时常含泪回顾自己走过的这20余年,竟是那样那样的无聊,那样那样的遥远而漫长。”“对我们来说,冥想的状态,有如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我们这帮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冥想的,好像我们是用不着冥想什么的,但是在西海固,有少许土里刨食的人,少许识不了几个大字的人,却真的全副身心的在做着冥想的事,有人为了更好的想一些事情,甚至离妻别子,在偏僻处寻一个洞穴,日日月月在里面苦思冥想,这样的人不劳多问,只要有机会见到,从他们的脸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种冥想的痕迹来。”他对能冥想的人深深敬重,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充满反思。知识分子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冥想者的神性区别于常人,带有神的光辉,而且这种神性会从容貌上表现出来。“因此虽然身忙神乱,难得冥想之福分,但真的冥想者,我还是见过的。这也使我有了一点手段,见到人时,从一张张面目上也能看出些许端倪来。”在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作为回民族一分子的宗教情怀之间,石舒清更倾向于做精神和灵魂神性的追寻者。
石舒清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拱北。他的村子里有两个拱北,就是说有两个圣徒墓在他们村。拱北在这里是一个完全圣化的空间,是安顿灵魂的所在,是信仰者渴慕和神往之地——众生们无条件朝圣使精神得以皈依的地方。四处的人到这里上坟沾吉,也有人在这里建了小房子居住,化浊为清,修主归己。教众对拱北,充满了圣洁的期待,有一种“朝圣”般的庄严。作品中的人物如果对尘世生活已经厌倦了,就将自己置于拱北——去领受心灵的净化。现实中的不安与烦躁常常让“我”内心黯淡、焦虑,产生乞求超脱的心境,“我”就特别爱独自到拱北上去转悠。在短篇小说《风过林》中,作者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表达了这一思想:“毕竟身子在这世上混着,有很不洁净的一面。有一个阶段我沉沦罪恶,暗无天日,使我觉得我和一个四肢着地而行的野兽也差不离了。到墓地里去我得好好洗洗自己,这样洗却了一些使我软弱使我惶恐的东西,我心里对付的力量就加强了。”对于信徒们来说如果能一生敬守拱北,过上深山老林、上人墓侧、经卷香炉的生活,将是至高的荣誉和享受。在《短篇二题·贺家堡》中,杨万生老人把他的小孙子出散到拱北上,成了个出家人。这个娃娃后来继承了杨老人家的衣钵,成了影响一方的教主。《出行》中小满拉因为生病哪里都治不好,但到了拱北上就奇迹般地好了,先后几回都是这样子,后来他父母就把他出散到了拱北上,也成了出家人。“出散”是回族人对信仰彻底皈依的一种体现方式。石舒清向往“出散”后的简单的生活方式,但现实中石舒清受到种种约束做不到“出散”,只能在精神上向往“出散”。这种宗教情怀在石舒清那里没有刻意地审美化和艺术化,仅仅是他思想的真实展现。
在西海固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不少圣徒式的角色周游其间。石舒清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出发叙述了这些“周游其间”的“圣徒式的角色”。这些人物的身上都有着圣者的品性,他们的生命被来自“神性”的阳光所照射,仿佛镀金一般,成为他人和子孙的榜样。这些“圣徒式的角色”的突出代表是石舒清笔下的“老人家”形象。宁夏大学教授郎伟曾剖析过他笔下的这一系列形象。石舒清“对现实人生的叩问,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当中老人系列形象的精心刻画上。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他总是不自觉地将秉性善良、宽厚,具有强大坚忍的生命力量的老人与惜懂无知的少年人放在同一个现实世界中来进行艺术对比。通常的结局是,在少年人那双浑茫天真的眼睛里,爷爷和奶奶一辈人活得那样的纯粹、高贵、人格饱满而丰富。他们朴素的生命和多灾多难的人生之间并没有形成无边浩荡的悲怆之海,相反,以欢喜心看待人生的平静心态、超脱人世苦难的执着信念,却使他们面对任何社会灾难和人生命运的惊涛骇浪时都能镇定自若,神态安详。”就如郎伟所说的,石舒清总是不自觉地在小说中由衷地赞美着回回民族当中的老一代人,在这些“老人”的艺术形象之上,寄托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某种思考。
石舒清的代表作是《清水里的刀子》。在这篇小说中,马子善老人送葬完老伴,正要走出墓地时“似乎听到一个苍老而又稳妥的声音附在自己的耳边轻轻说,好啊,老东西,你命大,让你又逃脱了,那么就再转悠上几天,再转悠上几天就回来,这里才是你的家。”人的家在彼岸,彼岸的家才是每一个人永远的家,是每一个人终极的归宿。每一个在世界上游玩的孩子都要回家。在现实与信仰之间,石舒清没有被世界迷惑了眼睛,放弃了本源,他相信纯洁的信仰是道德完善、心灵净化的清洁动力,是获得圣洁、高贵和从容,抵达彼岸,提升和超越世俗人生的途径。于是宗教精神成为石舒清小说的精神底蕴。我觉得石舒清小说的宗教性首先取决于石舒清本人的宗教性,他对自己民族宗教的领悟和敬意,使他能对自己民族的命运与灵魂真正地接近、发现和感知。伊斯兰宗教精神成就着石舒清的文学世界。石舒清带着一种敬畏神圣的心写作,叩问现实,进行灵魂的告白,建构起了自我文学的深度。
三、背离与融合:石舒清笔下两个世界的关系
在石舒清的笔下,现实世界是凡俗的,充满人间烟火;宗教的世界是神圣的,清洁得一尘不染。回回民族就生活于其间,做着从此岸到达彼岸的挣扎和超越。现实如此沉重,以至于精神沉沦灵魂无法飞翔。此时这两个世界之间是抵牾的,凡俗的追求冲击着对神性的向往。《声音》中的尕嘴老汉可以说儿孙满堂了,后来老人摔断腿失去了生存能力,他被儿孙们抬进放牲口草料的屋子里,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在屈辱中等待死亡。看到这种情形,不由得疑惑,这不是一个信仰的社会吗?不是宗教让人彼此相爱,不离不弃吗?然而神性的追求有时却难以抵御现实、生存、物质等等对人的逼仄,甚至连信仰的虔诚都需要世俗的表达方式。《清水里的刀子》中言及,入土亡人都有着一个罪人的身份,入土后冥冥处就开始拷问他(她)的罪过。这时就要以献祭的仪式——“举念”来搭救亡人。但是“举念”什么呢?“举念”一头牛,还是一只羊?无论“举念”什么在安拉那里都是一样的,心意到就行了。但是世俗中,牛较羊贵重,“举念”一头牛更显虔诚。于是家里的那头年老的唯一的耕牛便被“举念”成搭救亡人的献祭,马老汉不忍,又执拗不过儿子,因为这样更能“对亡人当回事”,也是很有面子的事。小说中的“搭救”仪式中无疑有着强大的世俗的力量牵引:谁“举念”的东西价值贵重谁就被认为虔诚。“举念”的犹疑体现了物质有限的生存和以凡俗的方式体现神性虔诚的标准之间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种冲突中,已内化为回族民众的道德准则的宗教情感,不断地矫正、制衡着被世俗所影响的日常生活,指导着人的心灵穿越凡俗的世界向着光的所在艰难前行。《节日》中环环媳妇在为一个近80岁的老奶奶剪鞋样时被老人的一对银镯所吸引,产生了抢走那对银镯子的“惊心动魄”的欲望。她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感到自责,隐隐记起老人曾说“没有舍散心时心里黑暗着,一起念舍散,心里亮开了一条大路”。于是,她执拗地向丈夫要了一只自己精心喂养的山羊随大家一起将其舍散到石头山的拱北之上,当其他的女人向她投以崇拜的眼光时,她“又不自禁生了一丝骄傲,但她立刻就掐灭了,她知道在这里骄傲是有伤害的”。人性和神性在冲突、在交织,神性最后取胜利,环环媳妇成了一个清洁的人,焕发出神性的光彩。
当然,这两个世界最理想的状态是融合状态,也是石舒清最欣赏的状态。长篇小说《底片》中的姨奶奶红颜薄命、迈入老境时过着寄人篱下、无依无靠的隐忍的生活。然而她是教门方面最虔诚的人:只食清真食物、使用洁净之水,严格按时封斋,“每天半夜里起来,燃一根香秉在手里,低着头默坐到天亮。”我“能够清楚地记得老人在深邃宁静的长夜独对清灯长香的垂首静坐,清楚地记得老人学得点经后脸上的喜悦与幸福、超然的宁静与闲适。”生活宗教化、宗教生活化。神性擦亮了姨奶奶每一个漂泊、平淡的日子。《清洁的日子》中,母亲扫屋要选一个好日子,礼拜四或礼拜五,因为礼拜四是盼舍拜,礼拜五是主麻日。每当扫屋的日子,“母亲就像新娘一样喜悦而振奋”,“夜的巨翼还没有完全收起”,她就已经起来并洗毕大净了。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后,“还烙几个油馕,一遍遍在父亲耳边轻着声音唤他醒来,请他点几炷香,念一章《古兰经》上的索勒,再把油馕口道了……等父亲念毕索勒,口道罢油馕,母亲觉得扫屋才可以开始”。生活的项目又是宗教的仪式,信仰的光亮使凡常的生活变得丰富、充满意味。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挣扎、同一,是每个伊斯兰信仰者必经的心路历程,是民族内省灵魂的真实记录。在石舒清那里,二者是“皮皮子”与“嚷嚷子”之间的关系。小说《灰袍子》中“我的叔叔”是个生意人。但按照叔叔的说法,这“只是一个表皮皮子,是度世的人不得不有的一个扮相。”但认为“人好像一辈子都是花费在了这个扮相上,其实这个扮相是假的”。叔叔还说,每个人都有个“内瓤瓤子”,这个“内瓤瓤子”很贵重,“只有少数受到造物主特别拣选的人,才能觉知道自己的这个内在”。世俗世界就是“表皮皮子”的世界,宗教世界就是“内瓤瓤子”。今世与来生,来生才是重点,“内瓤瓤子”的世界更重要。人大都舍弃了内瓤瓤子,在这个皮皮子的世界上挣扎,挣下的好光阴只是一个眼欢喜。正是源于对民族信仰的真挚认同,石舒清赞美着迈向彼岸的今生的所有努力。
两个世界,两种身份的写作,石舒清来说是并行不悖的。虽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让他偶有质疑(例如对于柳阿訇,作者提到他时充满敬意,但是对他神神叨叨治病的描写却不置可否),但是总体来说石舒清视点的转换或外在或内在自由柔韧。这两种身份的写作在石舒清那里不是撕裂的。作为受到现代知识哺育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回民族的一员,这一双重角色决定了石舒清生命意识与宗教意识的兼容。石舒清用进步的人文眼光审视今生,今生有着太多的欲望和恶、倾轧和麻木。这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审视和打量。面对现实,他同情而隐忍。宗教的世界是作者理想的境界,寄托着他作为回回民族一分子的关于民族神性的理想,也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理想——神性的生存。这时的视角是内在的,尤其当他把那少数的圣者作为榜样时,他的目光是仰望的。知识分子身份让他客观看待本民族,怀抱着批判、同情和爱;宗教情怀让他高扬精神的旗帜,灵魂安宁。于石舒清而言世俗幸福,精神有归宿,应该是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吧?所以这两个视角内外互补,没有非此即彼的排斥与纠结。由这两个视角产生的理想世界,也应该是并行、互补、互融的两个空间:用信仰擦亮、提升、人生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进到高度和谐美满的人生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决定了石舒清怀有的是一种宗教情怀,而非宗教般的情怀。宗教般情怀仅仅意味着人生的悲悯,宗教情怀则认为宗教的神圣是人类该追求抵达的最终家园。那个地方不仅仅是,而应该是人生最终该去的地方。
作者简介: 沈秀英(1973—),女,山东莱州人,讲师,北京大学博士,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民族文学研究》、《宁夏社会科学》、《文艺评论》、《黑龙江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
值班编辑:和亚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