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神话学文明探源的语言路径|论文
摘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与历史学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口传时代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材料与认知的原因,导致神话与历史难以分辨,为此在文明探源中需要通过神话学语言路径,廓清和打通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神话与语言的系统性,即在语言路径中既要考虑神话文本之间以神名或类型为线索构成的系统,又要顾及以语音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成的另一个系统,并将二者结合研究以提高其阐释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神话学语言路径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文明探源;神话学;语言考证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作为主力学科,贡献巨大,有目共睹,但其他学科也能在此工程中作出贡献,神话学便是其中之一。神话学探源有多种研究路径,语言路径就是其中之一。
一、文明探源需要神话学
文明探源在诸多学者眼里,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分内的事,似乎与神话学没有关系。这一认知主要是受到神话与科学、历史被视为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神话与科学、历史向来被视为相对立的两极,神话一词含有很大成分的贬义,代表非逻辑的、故事的、幻想的,与不真实、不理性等看法等同,而科学、历史代表逻辑的、理性的、严谨的。但现实中的神话与历史或科学并非那么※渭分明,神话与历史、科学具有交叉重叠的区域。
真实与否的辨别并不容易,有的故事真假不是那么清晰。正因为这样,神话学与历史学就有一些重叠部分,重叠部分主要在关于上古时期一些人物的故事。关于这些人与事,有人认为是神话,而有人认为是历史。举个关于黄帝的例子,对黄帝的怀疑自古就有,比如西汉戴德编著的《大戴礼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日,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人是不可能活三百岁的,春秋时代的宰我就对黄帝的存在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现在,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提出了著名历史形成的“层累说”,认为中国的上古史大多是后人一步一步不断积累造成的,具体来说,在西周的时候,人们传说的最古人物只是大禹,到了春秋,增加了尧、舜,再往后到了战国,又增加了黄帝和神农。可见顾颉刚又从另一视角对黄帝的存在提出质疑。正因为对这些传说人物聚讼纷纭,有的视为神话,有的视为历史,神话与历史的交错难分难解,所以探源工程需要神话学的参与。
在中国神话学与中国历史学的交叉中,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一系列人物都存在争议,其牵涉面十分广泛而深远。叶舒宪提出了“神话中国”与“神话历史”的概念,认为神话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神话与历史的交错与杂糅。“神话中国”的概念强调了中国的文化一直被神话基因所充斥,与西方诸多国家不一样,“它并未像荷马所代表的古希腊神话叙事传统那样,遭遇到‘轴心时代’的所谓‘哲学的突破’,而被逻各斯所代表的哲学和科学的理性传统所取代、所压抑。唯其如此,神话思维在中国决不只是文学家们的专利”。“研究实践表明,神话作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一种概念工具,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和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这种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因而,不光是学习文学要从神话开始;要进入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神话历史。”
另外,考古学与历史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人类文明的传承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的、文字的、器物的,等等。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因此发掘出来的很多器物没有文字说明,难以解释。历史学重视文献,对无文字历史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时间长短来说,无文字历史要远远长于有文字历史。有文字的传统是小传统,无文字的传统是大传统,而许多文明的起源,都在无文字时期。神话学在研究口头传统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语言路径的理论机制
神话学与历史学具有重叠领域,这是神话学可以在文明探源上作出贡献的基础。那么神话学是否具有探源的能力呢?虽然神话学研究给人一种荒诞的印象,但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手段并不荒诞,甚至远远超出一般人文学科的带有很强主观性的路数,比如叶舒宪提出了以四重证据法来研究神话,成果显著。在此基础上,叶舒宪进一步提出了“N级编码”理论,与四重证据法几种元素的并列关系相比,这一理论强调几种元素之间时间上的历时关系。由此可见,神话学的研究偏重于科学性,而不是带有很强主观性类似于审美的路数。
神话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讲都是在探源。有意思的是,神话自身就有一类“探源”性质的内容,即起源神话或创世神话。这类神话中,最为“懒惰”的一种便是将事物的起源归于某一个神,比如将太阳与月亮的形成归因为某一位始祖神创造的。正因为这样,这类起源神话往往被视为虚妄的、不真实的、非历史的、与科学相悖的。所以,这类神话内容表面上是阐释事物的由来,但却不被认可,不能直接作为我们探源的证据。但是,很多神话内容的形成,并不都是古人将某一事物的起源随意附会到某一位神的头上。换言之,有一部分神话一开始并不离谱,其故事的本源存在一定真实性,是符合逻辑的,只是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变得离谱、不符合逻辑了。
为什么说神话中很多离谱、不符合逻辑的内容是在演变中形成的呢?原因是复杂的,不过语言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主要是语言疾病导致的。麦克斯·寥勒提出过著名的神话形成语言疾病说,一方面是表达方式的误解,另一方面是词汇的误解。麦克斯·寥勒认为古人自有其独特的表述方法,但由于时间久远,后人不理解,就形成了神话。关于表达方式的误解,可以用上帝以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之神话来说明,麦克斯·寥勒在阐释这则神话的诞生时说:“‘当我们用现代语言说某个东西与另一个完全一样时,希伯来人则说是某物的骨头,阿拉伯人则说是某物的眼睛。’……如果亚当用现代语言说话和思考,他就会向夏娃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但这一思想,用希伯来语表示则成了‘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说,上帝以亚当肋骨创造夏娃的神话,是对“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表达方式的误解。所以,很多神话表象看似荒唐,其实这是由于语言疾病造成的,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述。
语言疾病更多表现在词汇误解上。麦克斯·寥勒举了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为例,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本义已经不明确了,不过在梵语中有一个对应的词pra-matyas,可译为钻木取火的人。麦克斯·寥勒推测,钻木取火的古老方法被人遗忘之后,人们不知道这个词的原义了,便望文生义编造了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这里举两个中国神话的例子,一个是“女娲补天”神话,一个是“黄帝四面”神话。一提及女娲补天,人们自然会想到天空出现了漏洞,于是女娲炼石补天。不用说,这一内容极其荒诞无稽,和科学或历史几乎毫无关系。其实,女娲补天神话是语言误解导致的,所谓的补天,是指闰月的补天数,“单纯采用阳历或阴历都有缺点,古人便将两种历法合起来构成阴阳合历,即农历。农历要用闰月的方法来补齐阴历少于阳历的天数,这便是补天。补天数讹误为补苍天,演化出女娲补天神话”。之所以是女娲这位大神补天,是因为女娲为月神,阴历是根据月亮的圆缺盈亏变化来制定的,阴历的天数要少于阳历,那么阴历就得补,女娲由月亮拟人化演变为月神,再演变为掌管历法的人,补天之职便理所当然由女娲来承担。

再来看“黄帝四面”的神话。这一神话同样荒诞、不符合逻辑,一个人不可能有四张面孔。这也是由于语言疾病导致的,其实“黄帝四面”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导致的二分二至现象的故事化。在生活于地球北半球的人看来,太阳除了每天东升西落的运动之外,还要在一年中的冬至、春分、夏至、秋分这二分二至到达南、东、北、西四极,即四面。黄帝的原型是太阳,黄帝四面即太阳四面。这就是“黄帝四面”神话的来源。这里的“面”不是名词,不是脸面,而是动词,是“面临”“莅临”的意思,黄帝四面即黄帝(太阳)莅临四极。
语言疾病理论证明,有的神话背后隐藏着科学与历史的真实,即神话故事的本源。如果能掀开这些神话离谱的表象,探索到其背后所隐藏的本源,就能达到文明与文化溯源的目的,所以说,以语言的方法来探寻神话的本源是神话学文明探源的路径之一。
三、神话学语言路径的系统性
由于对语言的误解造成了对神话本源的误解,那么消除误解首先应该从语言入手。学术界关于黄帝的身份争议很大,很多学者认为他是神话人物,何新从语言角度来阐释黄帝的本源是太阳:“黄,《说文》指出其字从古文‘光’字,也读作光声。实际上黄、光不仅古音相同,而且都有光的语义。《风俗通》说:‘黄,光也。’《释名》说:‘黄,晃(日光)也。犹晃晃像日光也。’日光本色即黄色。所以古天文学中,日行之道,称作‘黄道’……凡此皆可证,黄、晃、皇、煌、光在古代音同义通,可以互用。所以,黄帝可释作‘光帝’。所谓黄帝、皇帝,其本义就是光明之神。”这一方法的简洁直观是显而易见的。
在神话溯源的研究上,类似以上的语言考证方法一直被广泛使用,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也有自身的短板,比如关于“黄”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唐代的司马贞认为黄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而“黄”的金文象蝗虫形,《汉典》认为当是“蝗”的本字,本义是蝗虫。这就牵涉到“黄”到底应该解释为“光”“黄色”还是“蝗虫”的问题,同样是从语言入手,孰是孰非就不好断定。另外,撇开其他角度不说,单纯就语音考证来说,也存在一定难度,比如要考证“黄”与“光”的关系,免不了要借助古音的构拟,而构拟的古音是否完全可靠是有争议的。目前古音构拟有王力、高本汉、郑张尚芳、李荣、邵荣芬等好几位学者构拟的体系,体系之间有所差异,使用谁的,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使用语言进行溯源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那么,这一研究路径怎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它的科学性呢?
要弥补从语言入手进行考证的短板,以神话的系统性与语音的系统性来对某种观点进行验证,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所谓神话的系统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梳理,一方面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神话系统,另一方面是神话类型上的体系。不论是哪一种,在阐释某一具体问题的时候,都要顾全其他相关问题的阐释。举例来说,顾颉刚曾经提出大禹的原型可能是虫的猜想,作为一种学术讨论,“大胆设想”本身无可争议,但这一猜想得顾全到与大禹有关的叙事,比如怎样解释大禹治水,尧舜禹的禅让又怎么解释?如果大禹是虫,那他的妻子涂山氏是什么?他所杀的防风又是什么?如果无法解释这些疑问,说明这一观点不适合作系统性的阐释,其可靠性就不高。在运用语言进行考证的时候,要考虑到系统的限定性,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考证的科学性。
这里再以对舜故事的阐释为例来说明神话系统性的限定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舜即帝俊,而帝俊是太阳神,这就意味着舜原本是太阳。这样的观点是否成立可先搁置,我们可以用与舜有关的故事系统来测试一下这一观点的阐释力如何。如果认为舜原本是太阳,那么怎么阐释“舜耕历山”?怎么阐释舜巡守四岳与“舜征四凶”?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是怎么回事?又怎么解释《稽瑞》里说的“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在不改变舜为太阳的基础上,能一以贯之阐释这些叙事吗?
笔者曾经阐释过“舜耕历山”故事原本是太阳在历法山的上空更替。论证的方法是通过语音的考证,证明“耕”是“更”的讹误,所谓的“舜耕历山”是从“舜更历山”讹误而来的。这一推论以舜原本是太阳为基础,历山可以解释为历法之山,即制定历法的山,也就是观测太阳运转的山,相当于现在的观象台所在的山。历法是通过观测太阳在历法山的上空不断更替产生的位置变化而得来的,这种更替也就是“舜(太阳)更历山”,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是口传,人们逐渐将太阳舜人格化,“更”又误解为“耕”,便产生了舜在历山上耕种的神话故事。有意思的是,《搜神记》关于舜耕历山的记载是这样的:“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这一记载非常诡异,按理说,舜在历山上耕作,应该收获五谷才对,传说却说他得玉历,也就是如玉一样宝贵的历法,这显然是故事本源的遗留。
我们可以认为“舜葬于苍梧之野”是指太阳下山。古人把太阳落山比喻为太阳死亡,而舜是太阳,太阳西坠故事化为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可以理解为星象代替了太阳的更替,也就是说,白天人们观测太阳的运转,晚上人们观测星象的运转。与“舜更历山”一样,“象”后来被讹误为大象,说大象帮舜耕种,或者说“象”是舜的弟弟的名字,他弟弟帮他耕种。
关于尧舜禹的禅让,我们同样可以解释为太阳的更替。古人传说天有十日,十个太阳轮流值班,即“十日代出”或“十日更替”。《山海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应该是十日轮替值班的原始传说。尧舜禹的禅让其实是十日轮流值班这一想象的故事化,而且这一神话故事不断地被历史化。当然这牵涉到尧、禹的本源也得是太阳,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不赘述,这里只是想说明假设舜的本源是太阳,是否能阐释清楚尧舜禹的禅让故事。
说舜的本源是太阳,又牵涉到舜巡守四岳的传说。《尚书·舜典》中有关于舜巡守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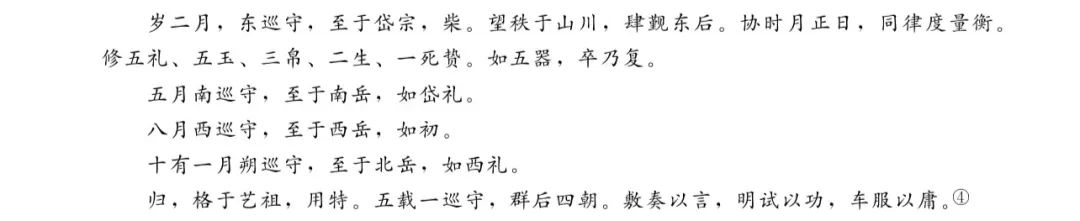
这其实依然是太阳运行的另一种传说变异。这段文字所记载的巡守在时间分配上是均衡的,二月在东,五月在南,八月在西,十一月在北。关于这一时间点,陆思贤认为与观象有关:“二月测定春分点,五月测定夏至点,八月测定秋分点,十一月测定冬至点。”这已经敏锐地指出了舜巡守四岳其实与历法有关,不过这巡守不是测定,而是指太阳在各个时间点分别到达了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和冬至点,即二分二至。
舜的著名事迹还有“舜征四凶”。《尚书·舜典》云:(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说的是舜征伐共工、驩兜、三苗、鲧四凶。这“四凶”可解释为“四穷”,也就是四极,其实就是太阳在二分二至分别到达四极。《尚书全解》补充了四凶的归宿:“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里四凶分别变成了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又与东南西北挂钩了,幽州、崇山、三危、羽山也分别是传说中处于遥远四方的山,这可以看出舜征四凶与舜巡守四岳其实是一回事。所以说,将舜的本源假设为太阳,能很好地阐释舜的诸多神迹,而且相互照应,互不矛盾,具有较好的阐释力。
神话系统性还可以从神话类型加以梳理。以上所说的舜巡四岳与舜征四凶,其实就是同一故事类型。同一故事类型的叙事在结构上相似,但故事人物往往有所变化。与舜巡守四岳、舜征四凶为同一类型的故事还有羲和驻守四极、黄帝四面。《尚书·尧典》里有关于羲和驻守四极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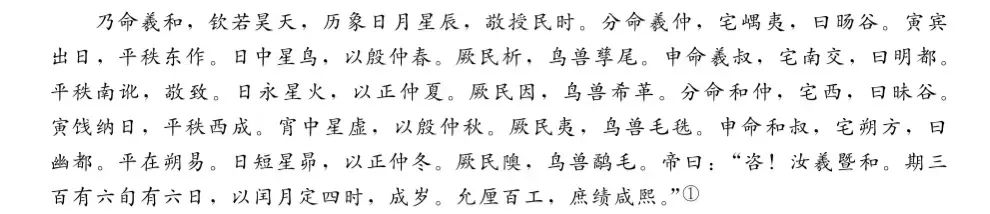
羲和是太阳神,在文献中依然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这与舜的本源可以对应。在此“羲和”被拆分为四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这属于神话的变异,他们四人分别驻守四极,这与舜(太阳)在四个时间节点分别巡守四岳、以及舜征四凶是同样的故事结构,原本也都是太阳在二分二至到达四极。另外,与黄帝(太阳)四面也是同一本源。上文已经分析过“黄帝四面”的来源,这里不再赘述。
上文从故事人物或故事类型来串联神话故事,以说明在阐释神话的时候要顾全神话故事的系统性。神话的系统性是网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果假设舜的本源是太阳,并以此来阐释“舜耕历山”,便涉及要以此来阐释舜征四凶、舜巡守四岳,这又牵涉到黄帝四面,从而又牵涉到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这么一层层关联下去,便成了一个网状的关系。这个关系网便是所谓的神话系统,在作神话阐释的时候,必须做到系统地观照,观点应一以贯之,一旦持有某一观点,就需要以此观点为基础来阐释系统内相关的神话故事。
除了以上分析的神话系统性,语音的变异也会构成系统。举例来说,汉语群目前有许多方言土语,一个词的古音已经发展变异成多个不同的音,比如“月”这个词,不仅目前各地的方言土语有很多不同的读法,现在的音与历史上不同时段的读音也可能不同,所有这些不同的音构成了一个系统。月亮是影响人类的最主要的自然物之一,关于月亮的神话多如牛毛,这其中就有关于月神的。月神的名称往往与月亮名称是一致的,只是由于语音的演变,我们很难察觉了,比如嫦娥是著名的月神,“娥”在某些方言里目前读[ŋo],而“月”的上古音构拟是[ŋod],显然“娥”就是“月”。由于语音的变异,导致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这样就不断分化成不同的月神。在神话研究中,女娲、涂山女、西王母、嫫母等都有被认为是月神的,那么,这种观点就需要结合“月”的语音体系来考虑。这里以女娲为例,在汉画像中,伏羲女娲的日月神格明显,伏羲身边经常画有一太阳,女娲身边经常画有一月亮。女娲不仅神格上与嫦娥一致,“娲”“娥”的读音也有一样的来源,“娥”可以读wo,而“娲”的声符也可以读wo,这就说明将女娲视为月神的观点处于“月”的语音体系之中,其可靠性得到增强。
上文提及为舞再的神让原本是十日轮流值班的故事化,再的本源也是太阳。因为“日”的语音体系其实与“月”的语音体系是同一体系,古人把日月都视为天的眼(目),宋金兰在《汉藏语“日”“月”语源考》中提出:“汉语和藏缅语言的‘日’和‘月’均来源于‘眼睛’一词。”也就是说,古人一开始在名称上不区分日月,后来才用变异出来的语音将日月区分开来。一个原始的语音,变异出不同的音之后,日月分别使用,日月被人格化,日月的名称便成了神的名称,比如“月”发展出女娲、端娥等月神来,而“日”发展出伏義、后弹等日神来。伏義、后弹在语音上也是对应的,“弹”目前读yi,“義”也曾经读yi,《说文解字》解释“義”字时说“从兮義声。”日月的名称由“眼”的古音发展而来的观点,从许多民族神话的材料可以得到支持,比如汉族的神话说盘古死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哈尼族的创世史诗《奥色密色》则说日月是由牛的双眼化生而成的,这种说法极为普遍。既然再的本源是太阳,他的妻子涂山女的本源应该可以被推测为月亮,有文献也说再的妻子是女娲,秦嘉谟辑补本《世本·帝系篇》云:“再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这说明涂山女即女娲,而女娲是月神。那么这一推测是否符合以上语音体系的限定呢?其实,涂山即蜍蟾,也就是月亮中的蟾蜍。在语音上,“蟾”与第一人称中的“朕”对应,而“蜍”与第一人称中的“余”对应。由此可见,虽然“涂山”名称变异很大,但都没有离开这一语音体系。以再的原型是太阳为基础,也能很好地阐释再杀防风的神话,防风与共工、逢蒙是同一系列的神祇,是雷神、水神。太阳神与水神、雷神在中原神话中历来是处于对立面的。
那么这个“眼”发展出来的日月语音体系是怎样的呢?无论是yi,还是wo,都是第一人称的音,第一人称代词中有一个“台”字,读yi。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日月的古音(眼的古音)在某一时间段与第一人称的古音相同,从“眼”目前的读音yan与第一人称“言”目前的读音yan相似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眼(日月)”的原始音与第一人称代词的原始音应当就是一致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余/予、言、俺、卬、朕、寡、台等的古音、现代音,官话、方言等所构成的语音体系,便是“眼”所发展出来的日月语音体系。日神月神的人物名称,都可以试着与这个体系里的音进行对比。
综上所述,神话学与历史学在研究领域具有重叠的部分,在文明探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考证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路径,但需要用系统性来加以约束,以增强其阐释的可靠性。
作者简介

吴晓东,湖南凤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神话学、南方民族口头传统。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4期
文章注释已省略
文章推荐:刘建波 图文编辑:吉一宁

